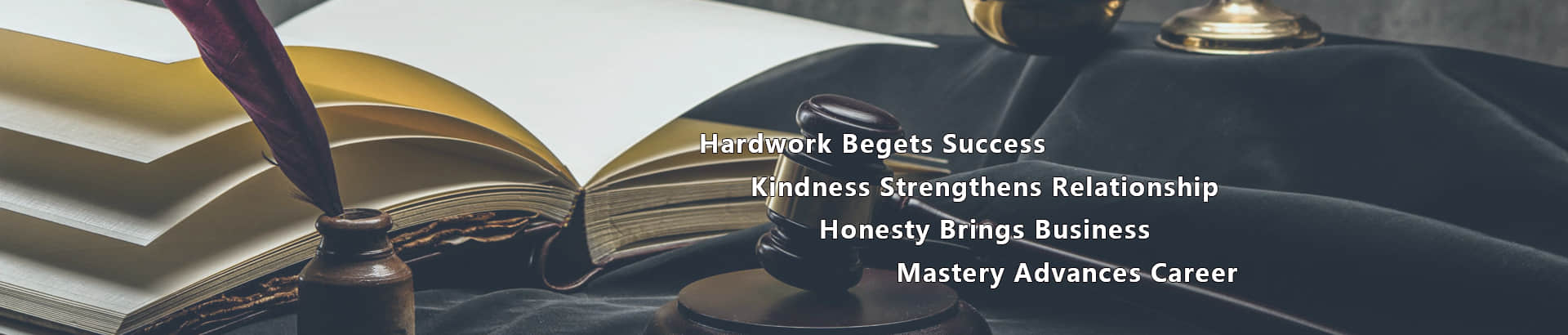NEWS
Publications
ๆต
่ฎบ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
TIME๏ผ2015-10-29 PUBLISHER๏ผADMIN
ๅญไฟ็บข
ๆ่ฆ๏ผๆๅฝ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ๅถๅบฆ็ป่ฟ็ผๆ
ขๅๅฑ๏ผๅทฒ็ปๅๅพไบไปคไบบ้ผ่็่ฟๅฑ๏ผไฝๆฏๅจ็ซๆณไธๅฎ่ทตไธญไป็ถๅญๅจ่ฅๅนฒ้ฎ้ข๏ผ้่ฆๆพๆธ
่ฎค่ฏ๏ผๅ ไปฅๅ็่งฃๅณใ
ๅ
ณ้ฎ่ฏ๏ผ 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๏ผ 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ไธพ่ฏ่ดฃไปป๏ผ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้้ข
ๆฃ่
ๅฐๅป้ขๅฐฑ่ฏ๏ผๆ ้ๆฏๆณ่งฃ้ค็
็๏ผไฝ่ฅๅ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๏ผไธไฝ่บซไฝๅๅฐๆๅฎณ๏ผ่ไธ็ฒพ็ฅไนไผๅๅฐๆๅฎณใๆๆถ๏ผ็ฒพ็ฅไธ็ๆๅฎณ็ปๆฃ่
้ ๆ็็่ฆๅฏ่ฝไผๆดๅคงใไบๆฏ๏ผๅจ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ไธญ๏ผ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ๅพๅพๆไธบๆฃ่
ๅๅ
ถไบฒๅฑๅ
ณๆณจ็้ฎ้ขใ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่ฝไธ่ฝ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ๆๆฒกๆๆณๅพไพๆฎ๏ผ่ฏฅๆ็
งไปไนๆ ๅ่ตๅฟไนๅฐฑๆไธบๅปๆฃๅๆนไบๆง็็ฆ็นใ
ไธใ 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็ฐ็ถ
ๆๅฝ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ปๅไบไธไธชๆฒๆ็่ฟ็จใ ใๆ้ซ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ๅ
ณไบ็กฎๅฎๆฐไบไพตๆ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่ดฃไปป่ฅๅนฒ้ฎ้ข็่งฃ้ใๅบๅฐไปฅๅ๏ผๆณๅพๅฏ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ฒกๆๆๆ่งๅฎ๏ผๅฏไธ็ไพๆฎๆฏใๆฐๆณ้ๅใ็ฌฌไธ็พไธๅไนๆก๏ผ“ไพตๅฎณๅ
ฌๆฐ่บซไฝ้ ๆไผคๅฎณ็๏ผๅบๅฝ่ตๅฟๅป็่ดนใๅ ่ฏฏๅทฅๅๅฐ็ๆถๅ
ฅใๆฎ็พ่
็ๆดป่กฅๅฉ็ญ่ดน็จใ”ๅ
ถไธญไธไธช“็ญ”ๅญ๏ผไผผไนๅ
ๅซ๏ผไผผไนๅไธๅ
ๅซ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ๅค่ต็่ฏดๆๆณๅพไพๆฎ๏ผๅคไธ่ต็่ฏดไพๆฎไธ่ถณใๅ ๆญค๏ผๅจๅธๆณๅฎ่ทตไธญ๏ผๆ็ๅฐๆน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ไธๆฏๆ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ๆ็ๅฐๆน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่ฝ็ถๆฏๆ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ไฝๆ ๅๅดไธ็ปไธใๆป็ๆฅ็๏ผๆณ้ขๅฏ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ๅคๅณ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ๆๆฅๆๅคใ้ปๆฐ็ญ่ฏ้พๅฒฉๅธ็ฌฌไธๅป้ขๅป็ไบๆ
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กไธญ๏ผ็ฆๅปบ็้ซ็บง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ๅคๅณ้พๅฒฉๅธ็ฌฌไธๅป้ข่ตๅฟ้ป็บๆปข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้15ไธๅ
๏ผ็็บ่ฑช่ฏๅ็ตๅญๅทฅไธ้จๅ0ไบๅป้ขๅป็ไบๆ
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กไธญ๏ผๆณ้ขๅคๅณๅป้ข่ตๅฟ็็บ่ฑช็ฒพ็ฅๆๅคฑ่ดน18ไธๅ
ใ[1] ไธบไบ่งฃๅณ็ฐๅฎๅญๅจ็ๅฏ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่ฏฅไธ่ฏฅ็ปไบ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้ฎ้ข๏ผๅๅฐ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ๅจๅธๆณๅฎ่ทตไธญไฝไบๆ็็ๆข็ดขใๅฆ2000ๅนดๅ
ๆๅไธๆฅ้ๅบๅธ้ซ็บง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้่ฟ็ใๅ
ณไบๅฎก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กไปถ่ฅๅนฒ้ฎ้ข็ๆ่ง๏ผ่ฏ่ก๏ผใ็ฌฌไธๆก่งๅฎ๏ผๅ
ฌๆฐๅ ๅ
ถไบบ่บซๆๅฉๅๅฐไธๆณไพตๅฎณ๏ผไฝฟๅ
ถไบบๆ ผๅฉ็ๆ่บซไปฝๅฉ็ๅๅฐๆๅฎณ่้ญๅ็ฒพ็ฅ็่ฆ็๏ผๅฏไปฅ้่ฟๆณๅพ็จๅบ๏ผ่ฆๆฑไพตๆไบบ่ตๅฟ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ๆๆ
ฐ้ใๅๅฆ2000ๅนด7ๆ11ๆฅๅไบฌๅธ้ซ็บง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ๆ นๆฎใไธญๅไบบๆฐๅ
ฑๅๅฝๆฐๆณ้ๅใ็ญๆๅ
ณๆณๅพ่งๅฎ๏ผ็ปๅๅฎกๅคๅฎ่ทต๏ผ้่ฟไบใๅ
ณไบๅฎก็ไบบ่บซไผค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กไปถ่ฅๅนฒ้ฎ้ข็ๅค็ๆ่งใ๏ผๅฏนไบบ่บซไผค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กไปถไธญ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้ฎ้ข๏ผๆๅบไบๅ
ทไฝ็่งฃๅณๆนๅผใ
่่ๅฐ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ๅญๅจ็่ฎธๅค็ฐๅฎ้ฎ้ขไปฅๅๆๅฝ็ๆณๅพ่งๅฎๅฐไธๅคๅฎๅ๏ผไธบไฟๆคๅๅฎณไบบ็ๅๆณๆ็๏ผๆ้ซ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ไบ2001ๅนด้่ฟไบใๆ้ซ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ๅ
ณไบ็กฎๅฎๆฐไบไพตๆ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่ดฃไปป่ฅๅนฒ้ฎ้ข็่งฃ้ใ๏ผไปฅไธ็ฎ็งฐใ่งฃ้ใ๏ผ๏ผๅฝๅก้ขไบ2002ๅนด้่ฟไบใๅป็ไบๆ
ๅค็ๆกไพใ๏ผไปฅไธ็ฎ็งฐใๆกไพใ๏ผใใ่งฃ้ใ็ฌฌไธๆก่งๅฎ๏ผ่ช็ถไบบๅ ไธๅไบบๆ ผๆๅฉ้ญๅ้ๆณไพตๅฎณ๏ผๅ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่ตท่ฏ่ฆๆฑ่ตๅฟ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็๏ผ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ๅบๅฝไพๆณไบไปฅๅ็๏ผ(ไธ)็ๅฝๆใๅฅๅบทๆใ่บซไฝๆ๏ผ(ไบ)ๅงๅๆใ่ๅๆใๅ่ชๆใ่ฃ่ชๆ๏ผ(ไธ)ไบบๆ ผๅฐไธฅๆใไบบ่บซ่ช็ฑๆใใๆกไพใ็ฌฌๅไบๆก่งๅฎ๏ผๅป็ไบๆ
่ตๅฟ๏ผๆ็
งไธๅ้กน็ฎๅๆ ๅ่ฎก็ฎ๏ผ(ๅไธ)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ๆๆ
ฐ้๏ผๆ็
งๅป็ไบๆ
ๅ็ๅฐๅฑ
ๆฐๅนดๅนณๅ็ๆดป่ดน่ฎก็ฎใ้ ๆๆฃ่
ๆญปไบก็๏ผ่ตๅฟๅนด้ๆ้ฟไธ่ถ
่ฟ6ๅนด๏ผ้ ๆๆฃ่
ๆฎ็พ็๏ผ่ตๅฟๅนด้ๆ้ฟไธ่ถ
่ฟ3ๅนดใ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้ฎ้ขๆป็ฎๆไบไธไธชๆๅจ็ๆ ๅใ ่ฝ็ถ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้ฎ้ขๆญฃๅจๅๅฐ็ซๆณไธๅธๆณๅฎ่ทต่ถๆฅ่ถๅค็ๅ
ณๆณจ๏ผไฝๆฏ็ฑไบๆณๅถๆฌ่บซ็ไธๅฎๅ๏ผๅๅ ไธไบบไปฌๅฏนๆไบ้ฎ้ข็่ฎค่ฏๅญๅจๅๆญง๏ผๅจ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้ฎ้ขไธไปๅญๅจ่ฎธๅค่ฏฏ่งฃไธๅๅทฎ, ้่ฆๆไปฌๆพๆธ
่ฎค่ฏ,็ปไธๆ ๅใ
ไบใ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ๅญๅจ็้ฎ้ขๅ่งฃๅณๆ่ทฏ
1.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่ฏ่ฎผ็่ฏๅ ้ฎ้ขใๅ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ๅ๏ผๆฃ่
ๅๅ
ถๅฎถๅฑ็ฉถ็ซ่ฏฅไปฅไปไน็็ฑ๏ผๅณ่ฏๅ ้ฎ้ข๏ผๅๅป็ๆบๆ่ฏทๆฑ่ตๅฟ๏ผ่ฟๆฏไธไธช้ๅธธ้่ฆไนๅพ่ไบบๅฏปๅณ็้ฎ้ขใ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่ฏ่ฎผ็่ฏๅ ๆ ้ไธค็ง๏ผ่ฆไนไพๆฎๅป็ๅๅ่ตท่ฏ๏ผ่ฆไนไพๆฎไพตๆ่กไธบ่ตท่ฏใไผ ็ปๆณๅญฆ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่ฅไปฅๅป็ๅๅ็บ ็บท่ตท่ฏ๏ผๆฃ่
ๅๅ
ถไบฒๅฑๅช่ฆ่ฏๆๅป็ๆบๆๅญๅจ่ฟ็บฆ่กไธบ๏ผๅฐฑๅฏไปฅ่ทๅพ่ตๅฟ๏ผ่ฏๆ่ดฃไปป่พ่ฝป๏ผไฝๆฏไธๅฏไปฅ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่ฅไปฅไพตๆ่กไธบ่ตท่ฏ๏ผๅฏไปฅ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ไฝๆฏ่ฆ่ฏๆๅป็ๆบๆๅป็่กไธบๆ่ฟ้๏ผๆๆไพตๆ่กไธบๆๅฏไปฅ่ทๅพ่ตๅฟ๏ผ่ฏๆ่ดฃไปป่พ้ใ ๆฏซๆ ็้ฎ๏ผๅจๅปๆฃๅ
ณ็ณปไธญ๏ผๅฏนๅคไบๅผฑๅฟๅฐไฝ็ๆฃ่
๏ผๆข่ฆไฟๆคๅ
ถ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่ฏทๆฑๆ๏ผๅไธ่ฝ่ฎฉๅ
ถๆฟๆ
่ฟ้็ไธพ่ฏ่ดฃไปปใไฝๆฏไพ็
งไผ ็ป็ๆณๅพ๏ผๆ ่ฎบ้ๆฉไพตๆ่กไธบ่ฏ่ฎผ่ฟๆฏ้ๆฉ่ฟ็บฆ่ฏ่ฎผ้ฝไธ่ฝๅฎ็ฐๅฏนๆฃ่
็ๅจๅ
จไฟๆคใ็ฉถ็ซ่ฏฅๆๆ ท่งฃๅณ่ฟไธช้ฎ้ขๅข๏ผๆๅญฆ่
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็ฐ้ถๆฎตๅฏน่ฟ็บฆไน่ฏไธญ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ไธๆฆไธไบ่ตๅฟ็ๅบ็ณๅทฒๅจๆ๏ผ็่ณๅๅก๏ผๅจไธๅฎๆ
ๅฝขไธไบไปฅ่ตๅฟ็ไฝๆณไธ่งๅ่ช็ถๆตฎๅบๆฐด้ข๏ผๅ ๆญคๅปบ่ฎฎ่ฟ็บฆไน่ฏไนๅฏไปฅ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ใ[2]ไบๅฎๆ็ๅฆๆญคๅ?ๅๅๆฏๅๆนๅฝไบไบบ็็บฆๅฎ๏ผๅฆๆๅๆนไบๅ
ๆ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บฆๅฎๅจๅๅ่ฟ็บฆ่ดฃไปปไธญ๏ผไธๅฆจไบๅๅ
่ฎธ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ใไฝ่ฅๆฒกๆ็บฆๅฎ๏ผ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ๅฐฑ่ฆๆๆณๅพไพๆฎใๆๅฝๅๅๆณๅนถๆฒกๆๆๆ่งๅฎ่ฟ็บฆๅฏไปฅ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ๆฐๆณ้ๅ่งๅฎ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ไนๅชๆฏไปฅไธไบบ่บซ็ธๅ
ณ่็ไพตๆ่กไธบไธบ้ใไปๅฝๅค็ๅธๆณๅฎ่ทตๆฅ็๏ผ็็กฎๅญๅจ็ๅ ่ฟๅๅๅ่่ขซๆณ้ขๅคๅณ่ตๅฟ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ๅ่ฟ็บฆ้็่ฅๅนฒๆกไพ๏ผไฝไธ่ฌ้ไบไปฅๆไพๅฎๅฎ็ไบซๅๆ่งฃ้ค็่ฆๅ็ฆๆผ็ญๆๅพ
็ฒพ็ฅๅฉ็ไธบ็ฎ็ๅๅใ[3]๏ผP282๏ผ้ฃไนๆฏๅฆๆๅฟ
่ฆไฟฎๆนๅๅๆณไป่่ฎฉๆฃ่
ๅๅ
ถไบฒๅฑๅฏไปฅไปฅๅๅ็บ ็บทๆ่ต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ๅข๏ผ็ฌ่
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่ฟ็งไฝๆณๅนถไธๅฏๅใ่ฅไฟฎๆนๅๅๆณ๏ผๅ
่ฎธ่ฟ็บฆไน่ฏไนๅฏไปฅ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ๅๅฟๅฟ
ไผ็ ดๅๆณๅพไฝ็ณปไน้ป่พๅฎๆดๆง๏ผๅนถไธ้ ๆไบบไปฌๆณๅพๅบๆฌ็ๅฟต็ๆททไนฑ๏ผๅผๅๆดไธบไธฅ้็้ฎ้ขใ ็ฌ่
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่ฟไธ้ฎ้ขๅฏไปฅๅฉ็จๆๅฝ็ฎๅ็็ธๅ
ณๆณๅพ่งๅฎๅ ไปฅ่งฃๅณใๆ้ซ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2001ๅนดใๅ
ณไบๆฐไบ่ฏ่ฎผ่ฏๆฎ็่ฅๅนฒ่งๅฎใๅฐ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ไธพ่ฏ่ดฃไปป่งๅฎไธบไธพ่ฏ่ดฃไปปๅ็ฝฎ๏ผๅป็ๆบๆ่ฆๅฏน่ชๅทฑๆฏๅฆๆ่ฟ้ๆฟๆ
ไธพ่ฏ่ดฃไปป——ๅฆๆๅป็ๆบๆไธ่ฝ่ฏๆ่ชๅทฑๆ ่ฟ้๏ผ้ฃไนๅฐฑๆจๅฎๅป็ๆบๆๆ่ฟ้ใๅ ๆญคๆฃ่
ไปฅไพตๆ่กไธบ่ตท่ฏ๏ผๆขๅฏไปฅๅฎ็ฐ่ชๅทฑ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่ฏทๆฑๆ๏ผๅไธ่ณไบๆฟๆ
็น้็ไธพ่ฏ่ดฃไปปใ่ฟๆ ท๏ผๅจไธ็ ดๅๆๅฝๆณๅพไฝ็ณป้ป่พๅฎๆดๆง็ๅๆไธ๏ผๆฏ่พๅฅฝ็่งฃๅณไบไผ ็ปๆณๅญฆไธญๆฃ่
ๅฏ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่ฏ่ฎผ่ฏๅ ็ไธค้พ้ๆฉ้ฎ้ขใ ไธ่ฏๅ ็ธไผด้็ๅฆๅคไธไธช้ฎ้ขๆฏ๏ผๆฃ่
ๅๅ
ถไบฒๅฑ่ฝๅฆไปฅใๆถ่ดน่
ๆ็ไฟๆคๆณใ๏ผไปฅไธ็ฎ็งฐใๆถๆณใ๏ผไธบไพๆฎๆ่ตท่ฏ่ฎผใๅฏนไบ่ฟไธช้ฎ้ข๏ผๆๅ
ณ้จ้จ่ด่ดฃไบบๆพไบ2000ๅนด3ๆ้่ฟๆฐ้ปๅชไฝๅ่กจ็ๆณ๏ผ่ฎคไธบๅปๆฃๅ
ณ็ณปๆฏไธ็ง็นๆฎ็ๆฐไบๅ
ณ็ณป๏ผ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ไธๅบ็บณๅ
ฅ“3.15”ๆดปๅจๅ
ๅฎน๏ผๅฆๅ็ฑๆญคๅผ่ตท็ๅฐ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ญๅไบไธ่ฌๆถ่ดน็บ ็บท็่ฏฏๅฏผๅฐๅฏนๅปๆฃๅๆน็ๅฉ็้ ๆไผคๅฎณใใๆถๆณใไธป่ฆ่ฐๆด็ๆฏไปฅ่ฅๅฉไธบ็ฎ็็็ป่ฅ่
ไธๆถ่ดน่
ไน้ด็ๅ
ณ็ณป๏ผ่ๅ
ฌ็ซๅป็ๆบๆๆฏๅฝๅฎถๅฎ่ก็ฆๅฉๆฟ็ญ็้่ฅๅฉๆงๆบๆ๏ผไธไปฅ่ฅๅฉไธบ็ฎ็็็ป่ฅไผไธๆๆฌ่ดจ็ๅบๅซใๅ ๆญค๏ผ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ๆฏไธ็ง็นๆฎ็ๆฐไบ็บ ็บท๏ผๅปๆฃๅ
ณ็ณปๆฏไธ็ง็นๆฎ็ๆฐไบๅ
ณ็ณป๏ผใๆถๆณใไธ้็จไบ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ๅค็ใ[4]ไฝๆฏ่ฟ็ง่ง็นๆๆพๅจๅฏนๅป็ๆบๆไฝไฟๆค๏ผๅฆๆไพๆฌก็ฑปๆจ๏ผไบค้ใ้่็ญ่กไธไนไธๅบ่ฏฅ้็จใๆถๆณใใ็ฌ่
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่ฟ็ง่ง็นไธไฝไธๅฉไบไฟๆคๆถ่ดน่
ๅๆณๆ็๏ผไธๅฉไบๅป็ๆบๆ็่ช่บซๅๅฑ๏ผไนไธ็ฌฆๅๅฝๅ็ๅธๆณๅฎ่ทตไธ็ซๆณ่ถๅฟใๅจๅฎ่ทตไธญ๏ผไธไบๅฐๆน็ๅธๆณๆบๅ
ณไธ็ซๆณๆบๅ
ณๅทฒๅฐ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ไฝไธบๆถ่ดนๅ
ณ็ณปๅค็ใๅฆๅๅท็ๅฝๅฎถๅฐๅฆๆฒๆดๅจ้ท้ฉฌๅฑ็็ฑๅป้ขๅฆไบง็งๆฝ่กๆธ
ๅฎซๆฏๆถ๏ผๅป็่ฏฏ่ดๆฒๆดๅฎซ็ ด่ ๆผ๏ผไธๅนดไปฅๅ๏ผๅๅท็้ทๆณขๅฟ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้็จใๆถๆณใๅฎก็ปไบ่ฟ่ตทๅป็ไบๆ
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บ ็บทๆก๏ผๆไธบๅ
จๅฝ้ฆไพ้็จใๆถๆณใๅฎก็ป็ๅป็ไบๆ
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บ ็บทๆกใ[5]2001ๅนด1ๆ1ๆฅ่ตทๆญฃๅผๅฎๆฝ็ใๆตๆฑ็ๅฎๆฝ<ไธญๅไบบๆฐๅ
ฑๅๅฝๆถ่ดน่
ๆ็ไฟๆคๆณ>ๅๆณใๆๅปๆฃๅ
ณ็ณป็บณๅ
ฅๆถ่ดน่
ๆ็ไฟๆค็่ๅดใๅ ๆญค๏ผๆฃ่
ๅบ่ฏฅๅฏไปฅไปฅใๆถๆณใ่ตท่ฏใไฝๆฏ้ดไบๅฐๆนๅธๆณๆบๅ
ณ็ไฝๆณไธ็ปไธๅๅฐๆน็ซๆณๆบๅ
ณ็ๆๅจๆงไธๅค๏ผๅ
จๅฝไบบๅคงๅธธๅงไผๅบ่ฏฅๅฏนๆญคๅๅบๆ็กฎ็ๅฎใ
2.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ๆฐ้ข็กฎๅฎ้ฎ้ขใๅฐฑๆฃ่
ไธๆนๆฅ่ฏด๏ผๅฏน่ตๅฟๆฐ้ข็็กฎๅฎๅญๅจ็้่ฏฏ็่งฃใๆ่ฎธๅคๆฃ่
๏ผ็่ณ่ฎธๅคๅพๅธ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ๅ
ทๆๅพๅคง็ๅผนๆง๏ผๅฝไบไบบ็ดข่ต็่ถๅค๏ผๆณ้ขๅค่ต็ๆฐ้ขๅฐฑๅฏ่ฝ่ถๅคใ่ฟ็ง่ง็นๆฏ้่ฏฏ็๏ผๅพๅพไผ็ปๅๅฎณไบบๅธฆๆฅไธๅฟ
่ฆ็ๆๅคฑ๏ผๅบ็ฐ่ตขไบๅฎๅธ่ตไบ้ฑ็ๆ
ๅฝขใๅฆ๏ผไธๆญๅฟ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ๅฎก็็ไธ่ตทไบบ่บซ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บ ็บทๆกไปถ๏ผๅๅ้ๅฅณๅฃซๅฐ็พๅฎนๆค่คๅ
ๅๅผ ๆๅไธๆณๅบญ๏ผ่ฆๆฑไธค่ขซๅ่ฟๅธฆ่ตๅฟๅป็่ดนใ่ฏฏๅทฅ่ดนใๆค็่ดน46726ๅ
๏ผ็ฒพ็ฅๆๅคฑ่ดน6ไธๅ
ใ็ปๆๆณ้ขไพๆณๅคๅณไธค่ขซๅ่ตๅฟๅๅๅป็่ดนใ่ฏฏๅทฅ่ดนใๆค็่ดน็ญ่ฎก7103.87ๅ
๏ผๅ
ถไธญ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ๆๆ
ฐ้5000ๅ
ใๆๅผๆกไปถ่ฏ่ฎผ่ดนไธ่ฏด๏ผๆฌๆกๅๅๆ่ทๅพ็่ตๅฟๆปๅ
ฑๅชๆ7103.87ๅ
๏ผๆฃ้คๅพๅธ่ดน3000ๅ
ๅ่ขซๅๅทฒ็ปไป็4010.69ๅ
๏ผๅๅๅฎ้
่ทๅพ93.18ๅ
ใ[6]่กจ้ขไธ็๏ผๅๅ่ตขไบๅฎๅธ๏ผ่ๅฎ้
ไธๅฅนไธบๅฎกๅคไปๅบไบๅคง้็ๆถ้ดๅ็ฒพๅ๏ผไธๅ
ถๆ่ท็่ตๅฟ็ธๆฏๅพไธๅฟๅคฑใ่ฟๆฏๅ ไธบ๏ผ่ฟ้ซ็่ฏ่ฎผ่ฏทๆฑๅฆๆๅพไธๅฐๆณ้ข็ๆฏๆ๏ผๅณไฝฟๆฏๅป็ๅไฝ่ดฅ่ฏ๏ผๆฃ่
็
งๆ ท่ฆๆฏไปๅพๅธไปฃ็่ดน๏ผๅๆ
ไธ้จๅ่ฏ่ฎผ่ดนใๅ ๆญค๏ผๆฃ่
ๅจๆๅบ็ดข่ตๆฐ้ขๆถ๏ผไธ่ฝๆผซๅคฉ่ฆไปท๏ผๅบ่ฏฅไพ็
งๆณๅพใๆณ่งใๅธๆณ่งฃ้ไน่งๅฎ๏ผ็ปผๅ่่ๅ็งๅ ็ด ๏ผๅๆ
ๅ็ๅฐ็กฎๅฎใๆๆๅฆๆญค๏ผๆฃ่
ๅๅ
ถไบฒๅฑ็็ดข่ตๆไผๅพๅฐ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็ๆฏๆ๏ผๆไผๅพๅฐๅป็ๆบๆๆฏ่พๅฅฝ็้
ๅ๏ผไนๆ่ฝๆ่ชๅทฑๅบๅฝๆฟๆ
็่ฏ่ฎผ่ดน็จไธๅพๅธไปฃ็่ดน็จ้ๅฐๆไฝ้ๅบฆ๏ผๆๅคง้ๅบฆ็ไฟๆค่ชๅทฑ็ๅๆณๆ็ใ
3.็ฒพ็ฅๆไผค็จๅบฆ็้ดๅฎๆ ๅ้ฎ้ขใๆๅฝ็ฎๅ่ฝ็ถๆฟ่ฎคๅฏ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ไฝ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็้ดๅฎๅญๅจ็ๅพๅค้ฎ้ขใๅ
ถไธ๏ผไผคๅฎณ่กไธบไธๆๅฎณ็ปๆไน้ด็ๅ ๆๅ
ณ็ณป้ฎ้ขใไธๅฐไปไบๆไผค็จๅบฆ้ดๅฎ็ๆณๅปๅทฅไฝ่
ๅ็ฒพ็ฅ็
้ข็ๅธๆณ้ดๅฎไบบๅๆๅฐ็ฎๅๅฎๆฝ็ใไบบไฝ่ฝปไผค้ดๅฎๆ ๅ๏ผ่ฏ่ก๏ผใ๏ผ1990ๅนด4ๆ2ๆฅๆ้ซ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ใๆ้ซไบบๆฐๆฃๅฏ้ขใๅ
ฌๅฎ้จใๅธๆณ้จๅๅธ๏ผๅใไบบไฝ้ไผค้ดๅฎๆ ๅใ๏ผ1990ๅนด3ๆ29ๆฅๅธๆณ้จใๆ้ซ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ใๆ้ซไบบๆฐๆฃๅฏ้ขใๅ
ฌๅฎ้จๅๅธ๏ผๆๆฌ ๅฎๅไนๅคใ“่ฝปไผคๆ ๅ”ๅ“้ไผคๆ ๅ”็ๆๆๆกๆฌพ้ฝ็นๅซๅผบ่ฐไผคๅฎณ่กไธบไธๆไผคๅๆไน้ดๅ ๆๅ
ณ็ณป็็ดๆฅๆง๏ผ่ฆๆฑๆๅฎณๅๆไธไผคๅฎณ่กไธบไน้ดๅ
ทๆ็ดๆฅๅ ๆๅ
ณ็ณปใ่ๅจ็ฎๅๅทฒๆๅบ็ๆไบ“็ฒพ็ฅๆ ๅ”ไธญ๏ผไป
ไปฅ่ขซ้ดๅฎไบบๅๆๅฎณๅ็็ฒพ็ฅ็ถๆไฝไธบๅคๅฎ่ฝป้ไผค็ๅฏไธไพๆฎ๏ผๅณ้ๅๆ่่ฝปๅ ๆๅ
ณ็ณป๏ผ่ฟๆพ็ถไธ“่ฝปไผคๆ ๅ”ๅ“้ไผคๆ ๅ”็ๅๅไธ็ฌฆใๅ
ถไบ๏ผๅๅบๆง็ฒพ็ฅ็
ๆฏๅฆๅบ็บณๅ
ฅ่ฝปไผคไนๅใไป็ฎๅ็ฒพ็ฅ็พ็
ๅ็ฑป็ๅๅฑ่ถๅฟๆฅ็๏ผไบบไปฌๅฏนๅๅบๆง็ฒพ็ฅ็
็ๆ็ๅ้่ฎฎ่ถๆฅ่ถๅคใไธๆน้ข๏ผๅจๅฝ้
็ฒพ็ฅไธ่กไธบ้็ขๅ็ฑปๆ ๅ๏ผICD๏ผ10๏ผไธญ๏ผๅๅบๆง็ฒพ็ฅ็
ๅทฒไธๆๆไธไธช็ฌ็ซ็็พ็
ๅๅ
ใๅฆไธๆน้ข๏ผๆฎ่ตๆ็ป่ฎก๏ผๅจๆๆ่ขซ่ฏๆญไธบ“ๅๅบๆง็ฒพ็ฅ็
”็ๆฃ่
ไธญ๏ผๆ50๏ผ
ๅทฆๅณ็่ฏฏ่ฏ็๏ผ่ๅฆๆ56๏ผ
็ๆฃ่
่ฝฌๅฝไธบ็ฒพ็ฅๅ่ฃ็๏ผ่ฟ่กจๆๅๅบๆง็ฒพ็ฅ็
็่ฏๆญๅ
ทๆ็ธๅฝ็จๅบฆ็ไธ็กฎๅฎๆงใ[7]ๅ ๆญค๏ผๅฏนๅพ
ๅๅบๆง็ฒพ็ฅ็
ๅบไปไธฅๆๆกใ้ดไบ็ฒพ็ฅๆไผค้ดๅฎๆ ๅๅญๅจ็้ฎ้ข๏ผๅญฆ่
ๅบๅ ๅคง็ ็ฉถๅๅบฆ๏ผ็ซๆณๆบๆไนๅบๅฝๅๆถ็ๅธๆถใๅ้ดๆๆฐ็็ ็ฉถๆๆๅฏน้ดๅฎๆ ๅไฝๅบ็ซๆณไฟฎๆนใ
4.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 ๅ็้็จๆณ่ง้ฎ้ขใ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ฉถ็ซ่ฏฅ้็จๅธๆณ่งฃ้่ฟๆฏ้็จๆกไพ็ๆ ๅๅข๏ผใ่งฃ้ใ็ฌฌๅๆก่งๅฎ๏ผ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ๆฐ้ขๆ นๆฎไปฅไธๅ ็ด ็กฎๅฎ๏ผ(ไธ)ไพตๆไบบ็่ฟ้็จๅบฆ๏ผๆณๅพๅฆๆ่งๅฎ็้คๅค๏ผ(ไบ)ไพตๅฎณ็ๆๆฎตใๅบๅใ่กไธบๆนๅผ็ญๅ
ทไฝๆ
่๏ผ(ไธ)ไพตๆ่กไธบๆ้ ๆ็ๅๆ๏ผ(ๅ)ไพตๆไบบ็่ทๅฉๆ
ๅต๏ผ(ไบ)ไพตๆไบบๆฟๆ
่ดฃไปป็็ปๆต่ฝๅ๏ผ(ๅ
ญ)ๅ่ฏๆณ้ขๆๅจๅฐๅนณๅ็ๆดปๆฐดๅนณใๆณๅพใ่กๆฟๆณ่งๅฏนๆฎ็พ่ตๅฟ้ใๆญปไบก่ตๅฟ้็ญๆๆ็กฎ่งๅฎ็๏ผ้็จๆณๅพใ่กๆฟๆณ่ง็่งๅฎใใๆกไพใ็ฌฌไบๅๆก่งๅฎ๏ผ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ๆๆ
ฐ้ๆ็
งๅป็ไบๆ
ๅ็ๅฐๅฑ
ๆฐๅนดๅนณๅ็ๆดป่ดน่ฎก็ฎใ้ ๆๆฃ่
ๆญปไบก็๏ผ่ตๅฟๅนด้ๆ้ฟไธ่ถ
่ฟ6ๅนด๏ผ้ ๆๆฃ่
ๆฎ็พ็๏ผ่ตๅฟๅนด้ๆ้ฟไธ่ถ
่ฟ3ๅนดใ่ฝ็ถ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ฉถ็ซ่ฏฅ้็จใๆกไพใ็ๆ ๅ๏ผ่ฟๆฏ่ฏฅ้็จใ่งฃ้ใ็ๆ ๅๅญๅจๆไบ่ฎฎ๏ผไฝๆฏใๆกไพใๅฑไบ่กๆฟๆณ่ง๏ผๆ นๆฎๅธๆณ่งฃ้็่งๅฎ๏ผๆๆๅป็ไบๆ
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่ช็ถๅบๅฝ้็จใๆกไพใ็่งๅฎ๏ผ่ตๅฟๅนด้ๆ้ซไธ่ถ
่ฟๅ
ญๅนดใไธๆๆๅป็ไบๆ
ไ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ไปฅๅๆฒกๆ็ณ่ฏทๅป็ไบๆ
้ดๅฎไ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๏ผๅจ็กฎๅฎ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ถ๏ผๅๅฏไปฅไธๅใๆกไพใไน้ๅถ๏ผๅบ็ฑๆณๅฎๆ นๆฎใ่งฃ้ใ็่งๅฎ้
ๆ
ๅ ไปฅ็กฎๅฎ๏ผ้ฃไน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ๆ้ซๅนด้ๅฐฑๆๅฏ่ฝ่ถ
่ฟๅ
ญๅนดใ่ฟๆ ทๆๅฏ่ฝๅบ็ฐไธไบๆช็ฐ่ฑก๏ผไธๆๆๅป็ไบๆ
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ๅฏ่ฝ่ทๅพ่พๅค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๏ผๆๆๅป็ไบๆ
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ๅ่ๅฏ่ฝ่ทๅพ่พๅฐ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ใ่ฟไธ่ฝไธ่ฏดๆฏ็ซๆณ็ไธไธช็ๆผใไฝ็ฌ่
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ๆณๅฎๅช่ฆๅ
ฌๅนณๅธๆณ๏ผ่ฟ็งๆ
ๅตไธๅบ่ฏฅๅบ็ฐใๆ็
งๆณๅพ่งฃ้“ไธพ้ไปฅๆ่ฝป”็ๅๅ๏ผๆข็ถ่พ้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๏ผๅป็ไบๆ
๏ผ่ฆๅใๆกไพใ็ๅถ็บฆ๏ผ่พ่ฝป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ไบฆๅบ่ฏฅๅใๆกไพใ็็บฆๆใ่ฟๅฐฑ่ฆๆฑๆณๅฎๅจๅฎก็ไธๆๆๅป็ไบๆ
ไ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ๆกไปถไปฅๅๆฒกๆ็ณ่ฏทๅป็ไบๆ
้ดๅฎไน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ๆกไปถใๅ
ทไฝ็กฎๅฎ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ฐ้ขๆถ๏ผๅฟ
้กป่่ใๆกไพใ็่งๅฎ๏ผๅฐฝ้ไฝฟ่ตๅฟๆฐ้ขไธใๆกไพใ็่งๅฎ่กๆฅใไฝๆฏไนไธๅฏๅฆ่ฎคๅจๆๅฝไธไบๆณๅฎ็ด ่ดจ่ฟไธๅค้ซ็ๆ
ๅตไธ๏ผ็็กฎไผๆไธชๅซๆณๅฎๅบไบๅ็ง่่ไธ้ตๅพช่ฟๆ ท็ๅๅ๏ผไป่ๅฏผ่ดไธๅ
ฌๅนณๆ
ๅต็ๅ็ใๅบ็ฐ่ฟๆ ท็ๆ
ๅต๏ผๆณๅพ่ช็ถ้่ฆๅฎๅ๏ผไฝๆณๅฎ็ด ่ดจ็ๆ้ซไธๅถๅบฆ็ๅถ็บฆไนๅบ่ฏฅๅ ไปฅๅผบ่ฐใ
5.“ๆ
็จ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”้ฎ้ขใๆๅญฆ่
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ๆๅฝ็ฎๅ็็ปๆตๅๅฑๆฐดๅนณ่พไฝ๏ผๅคงๅคๆฐไบบ่ฟๅคไบไธ็งๆธฉ้ฅฑๆฐดๅนณ๏ผๆ็็่ณ่ฟ่พพไธๅฐๆธฉ้ฅฑๆฐดๅนณ๏ผ็ปดๆๅบๆฌ็ๆดป้่ฆๆฏ้ฆๅ
่่็้ฎ้ข๏ผ็ฒพ็ฅ็ๆดปๆๅ ็ๆฏ้ๆๅฐ๏ผๅ ๆญคๅจไธ่ฌ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่ตๅฟไธญๅบๆ
็จ็ฒพ็ฅ่ตๅฟใ[8]็็กฎ๏ผ่ฏทๆฑ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่ฆๆ
้๏ผไธๆฆๆณ้ขๅคๅณไธไบๆฏๆ๏ผ็ธๅบ็่ฏ่ฎผ่ดนใๅพๅธไปฃ็่ดน้ฝ่ฆ็ฑๅฝไบไบบๆฟๆ
ใไฝ่ฏฅๅญฆ่
็่ง็นๆๅคฑๅ้ขใ็ฌ่
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ๆๅฝ็ฎๅ็ฒพ็ฅ็ๆดปๆๅ ็ๆฏ้ๆฏๆฏ่พๅฐ๏ผไฝๅฏน็ฒพ็ฅ็ๆดป็ๆ่ตไธ็ฒพ็ฅไธ็็่ฆๅบ่ฏฅ่ฏดๆฒกๆๅฟ
็ถ่็ณป๏ผๆไปฌไธ่ฝๅฆ่ฎคไธไธชไนไธไนๆ็ฒพ็ฅ็่ฆ้ฎ้ข๏ผไปปไฝไบบ้ฝๅบ่ฏฅไบซๆ็ฒพ็ฅไฟ้๏ผไธๆฆๅจ็ฒพ็ฅไธๅๅฐไผคๅฎณ๏ผ้ ๆ็่ฆ๏ผไธ็ฎกไป็ๆดปๆฐดๅนณ้ซๆไฝ๏ผๅๅบ่ฏฅ่ทๅพๅนณ็ญ็่ตๅฟ๏ผ่ไธๅบ่ฏฅๆไปไนๅทฎๅซใ
6.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็้้ข้ฎ้ขใๆๅญฆ่
่ฎคไธบ๏ผๆๅฝ็ๅป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ๅบ่ฏฅๆไธไธช้้ข๏ผๅฎ่ก้้ข่ตๅฟใๅจๆๅฝ๏ผๅป็ไบไธๅฑไบ้ซ้ฃ้ฉ็ๅ
ฌ็ไบไธ๏ผๅ ๆญคไธๅบ่ฏฅ่ฎฉๅป็ๆบๆๆฟๆ
่ฟ้ซ็่ดฃไปปใ[9]ๅจๅฝ้
ไธ๏ผๆ ่ฎบๆฏ่ฑ็พๆณๅฝๅฎถ๏ผ่ฟๆฏๅคง้ๆณๅฝๅฎถ๏ผ้ฝ่ฏๅพไฝฟ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 ๅๅ๏ผๅนถ็กฎๅฎๅ
ถๆ้ซ้ขใๆๅฝ็ฎๅไนๅฎ่ก้้ข่ตๅฟ๏ผไฝไธๅฝๅค็ธๆฏ๏ผๆๅฝ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้้ขๆๆพๅไฝ๏ผไธใๆกไพใๅฎๆฝไปฅๅ็ๆณ้ขๅคๅณ็ธๆฏ๏ผใๆกไพใ่งๅฎ็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้้ขไนๆๆพๅไฝใๅ ๆญคๆไปฌ็็ซๆณๆบๆๅฟ
้กปๅจๆข่่ๅป็ๆบๆ็ๅๅฑ๏ผๅๅ
ๅไฟๆคๆฃ่
ๅๆณๆ็็ๅๆไธ๏ผๅฏนๆณๅพๆณ่งๅๅบ็งๅญฆใๅ็็ไฟฎๆนใ
ๅ่ๆ็ฎ
[1]ๆฅๆ๏ผ่ฟๅนดๅ
ธๅ็ๅป็่ฏ่ฎผๆกไปถ[J] www.southcn.com/news/china/china01/200204031002.htm
[2]ไธๆตทๆน๏ผ่ฟ็บฆไน่ฏไธญๅคๅฎ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ขๅพฎ[J]๏ผ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ๆฅ๏ผ2001.11.14.
[3]ๅ
ณไปๅ๏ผ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ๆฐ้ข็็กฎๅฎไธ่ฏ็ฎ[M] ๏ผๅไบฌ๏ผไบบๆฐๆณ้ขๅบ็็คพ๏ผ2002.
[4]็ๆถ็ ๏ผ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ๆกไพไธๅบ็บณๅ
ฅ“3•15”[J] ๅไบฌๆๆฅ๏ผ2000ๅนด 3ๆ14ๆฅ
[5]ๆถฆไป๏ผ“ๆถๆณ”็ฎกๅพไบ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ๅ๏ผ[J]ๅฅๅบทๆถๆฅ๏ผ2001ๅนด02ๆ22ๆฅ
[6]้ๆบ้ฆใ้้ฃ๏ผ็ฒพ็ฅๆๅฎณ่ตๅฟไธ่ฝๆผซๅคฉ่ฆไปท[J] ๏ผ็ฆๅปบๆฅๆฅ๏ผ 2003ๅนด07ๆ29ๆฅ.
[7]้ฉฌ้ฟ้ ๏ผๅ
ณไบ็ฒพ็ฅๆไผค็จๅบฆ่ฏๅฎๆ ๅ็่ฎจ่ฎบ [J] www.angelaw.com/medlaw/psycho10.htm
[8]ๅพ็บขๅนณ็ญ๏ผๅปๆฃๅฉ็ไฟๆคไธ็ๅป็็บ ็บท่ตๅฟ[J]๏ผๆณๅพไธๅปๅญฆๆๅฟ ๏ผ2000(1).
[9]ๅ้ซใๆพ่ท่๏ผๅป็ๆๅฎณ้้ข่ตๅฟๅๅ็็่ฎบๆข่ฎจ[J] www.szlaws.com/viewnews.asp